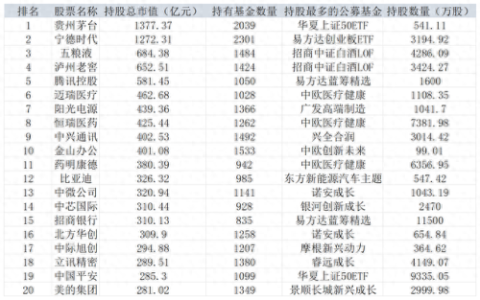楼兰,一个神奇的名字,一道留下太多疑问的谜题。在穿越时空的丝绸之路上,它曾经繁华胜锦,芳香可口的美酒和风情万端的美女,使得万里丝路充满无限诱惑。这种诱惑,沉醉了大汉的猎猎铁骑,痴迷了西域的冲天烽烟,点燃了千百年来无数考古专家和历史迷们心头熊熊不熄的八卦之火。特别是一百多年前随着楼兰古城遗址被探险家们发现于茫茫戈壁滩的罗布泊岸边以后,“楼兰热”风靡一时,一个又一个的楼兰之谜吸引着许多人甚至投入毕生精力进行解答。

皇后村村貌
楼兰文明从何而来?楼兰文明因何消亡?楼兰姑娘家在何方?……而“楼兰后人今在哪里”则成了“谜中之谜”。人们或许认为,如能找到当世之存在,便易于探究过往之隐秘。为破解此谜,一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和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记者所组成的科考队,曾于2005年前往新疆进行了一次《寻找古楼兰人后裔》的科考活动。这次活动通过央视等媒体作了详细报道,轰动一时。遗憾的是,虽然科考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也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判断,可对于最终的答案——古楼兰国的后人今天还存在吗?如果存在究竟在哪里呢?——却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
那么,神秘的楼兰国在消失于历史的尘烟1500年后,还真的有后人吗?到底在哪里呢?就在这时,一个同样具有神秘色彩的姓氏“鄯”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如同众多专家学者苦苦寻求楼兰的谜解一样,“鄯”姓的族人多年来也在不懈地寻找着这个冷僻的姓氏中间所隐藏的历史记号——为什么在华夏腹地的一个小山村里,几百口人世世代代会有这样的姓氏?历史学家想问“楼兰去了哪里”,“鄯”姓族人想问一声“我们从哪里来”。于是,就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时间结点上,两个问题碰在了一起:楼兰-鄯善-鄯姓!
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不需要怀疑这几者间的必然逻辑关系,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更多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来证明这种关系的天然存在。事实上,细加搜寻,这些资料和证据竟是翩然呈现,豁然眼前。
正所谓,无心望断西楼月,却待东山似锦云。也许我们错失了不少的宝贵岁月,但终究我们没有再失去动人的风景。
族自楼兰为“鄯”姓
姓氏之于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作用,犹如发肤之于身体、花叶之于树木。在人文之初,姓与氏各有其义,是相区别的,秦汉以后,二者合而为一,成为每个华夏人血脉相因的终生标记。有专家 作过统计,中国正在使用和曾经用过的姓氏有两万多个,而“鄯”作为其中的一员,似乎因其冷僻和人数少被忽略了。《百家姓》《千家姓》中没有录入,笔者在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祠堂谱牒里也没有找到踪影。在近年来由当代姓氏学者编著的几种大辞典里倒是将之收录,但记录极其简单,说明编著者也未甚悉鄯姓的源流。
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鄯姓在中国有多少人口?主要分布在哪里?笔者曾经在一本人口年鉴上看到过,全国鄯姓人口八百多,大多定居于山西省,其中五百多口居于山西省的盂县,而在盂县说到姓鄯,自然便是皇后村的人了。纵然零散居于别的乡村者,其父祖辈也是从皇后村迁出去的。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现在在北京、太原以及全国一些省市零星出现的鄯姓者,据笔者所知,基本上是近些年来从山西及盂县的鄯姓族中通过高考出去的,工作后定居新的城市,但他们的根脉是非常清晰的。
通过查阅地方志,可以知道,鄯姓与皇后村是连为一体的。《盂县志》上如此记载:传说古时此处有一姓鄯少年,选为太监进入皇宫,服侍皇后,数十年后鄯病死,皇后念他忠心,赐其村名为“皇后”,后演变为“黄候”(可能是出于避讳封建朝廷的“皇后”),清末民初,复称皇后。再据县志,在元朝时期,皇后村就存在了,而且村子的名字就是现在的“皇后”。由此而知,在元朝时,鄯氏一族便已定居于皇后村。根据资料记载,这时的鄯氏一族都属于汉民族。

古戏台
而在元朝末年还发生过一件事,对于鄯氏后人也是影响很大的:据盂县鲍氏族谱记载,鲍氏祖先是蒙古人,始居蒙古,多为元朝重臣,入主中原后,在盂就任官职。元朝末年,为避战祸,子孙分别与当地汉族女子联姻,改姓为孙、鲍、邢、鄯,分居盂境四地(孙姓住城西白水、鲍姓住元仇堡即元吉村、邢姓住寺底神泉、鄯姓住招贤皇后),并且盟约,要互相联系,永为一家,不能互相联姻等。另有记载,塔海,字天祥,蒙古族人,官至太原府事,子孙居盂之白水村,元末改姓孙。如今,盂县东白水村被确定为山西省唯一的蒙古族聚居村,村中孙姓的蒙古族占到全村人口的近四成。而其他三个与之相类似的村子尽管没有明确分出汉族与蒙古族的人数,但汉蒙两族相互融合繁衍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综上,对于皇后村的鄯氏一族,因为蒙古族女婿的加入,自然也融入了蒙古族的血统。
其实,华夏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本就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对此共识不作赘述。而因为鄯姓祖先更为游离动荡的悲壮历程,这中间的民族相融更为普遍。但归根到底,仍是堂堂炎黄后裔,磊磊华夏子孙。关于这一点在下一章节还将详述。
继续上溯,来到隋唐,又有发现。在我国历史上,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人迁徙流入并定居中原经历过两个高峰,一是北魏时入居洛阳。史载,当时流寓洛阳者,“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二是唐代西域人入居长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先生在1930年代完成的力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写道:“又鄯善人至中国姓鄯氏,前贤论及西域姓氏,从无注意及此者。近洛阳出土鄯乾墓志,卒于魏永平五年(公元512年);车师前部王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墓铭,卒于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是为六朝时入中国之鄯善人。又鄯昭墓志,卒于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其祖官于北周,父官于隋:是为唐代入中国知姓名之鄯善人。以俱卒于洛阳,长安尚未之见,兹姑不赘。”这三位不同朝代的鄯姓者,他们的墓都是在河南洛阳发现的,而在唐代的都城长安还没有发现。

200多年历史的油松
鄯乾墓志是1931年在洛阳老城东北后沟村东北的关帝庙后出土的,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还是一件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据历史学家考证,鄯乾的身份非一般,他是正牌的王子王孙,其祖父是鄯善王比龙,父亲是鄯善王真达,鄯乾是真达的长子。这个时候的中国北方正是北魏迅速崛起的前期,魏军四处征伐,所向无敌,统一了北方,又将国都从平城(山西大同)迁至河南洛阳。反观远在西域的鄯善国,国衰势弱,强敌环伺,为了保住王国不被覆灭,鄯善王多次主动遣使纳献于北魏,甚至让王弟、王子王孙入魏作“质子”(人质),同时,鄯善王也积极接受北魏授予的官职,在北魏皇帝的领导下继续维持其在西域的政权。鄯乾就是以“人质”的身份入侍北魏,不过他在北魏似乎没有受到歧视,他“以王孙之望”,先后担任北魏的员外散骑侍郎、辅国将军城门校尉、征虏将军安定内史,不但有较大权力,还身份贵重,常跟随皇帝左右。据墓志载,鄯乾寿达44岁,卒于公元512年,也即他生于公元468年。从他入侍北魏到卒于洛阳,正赶上了北魏的迁都(公元493年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事。根据史书可以推断出鄯乾入侍北魏当在493年迁都之前,这是因为在此前一年即公元492年,鄯善国发生了近乎亡国的重大变故(有关鄯善国最终亡国的准确时间,历史学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492年无疑是一次极其重大的改变,即使国残未亡,可也是奄奄一息、势如危卵)。史书载:时年,位于北部的游牧民族高车(又称“丁零”)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下,与柔然争夺塔里木盆地诸国,击破鄯善。南齐使者江景玄亲眼目睹“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一说鄯善从此灭国。因此鄯乾入侍北魏不可能是在国破之后才发生的,应该早于492年,否则他作为“人质”入侍就没有意义了。这次迁都,适逢秋雨连绵,北魏几十万大军从平城(大同)一路南下,道路泥泞,备尝艰辛,整整走了一个月才到达洛阳。作为随侍皇帝左右的鄯乾便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而鄯乾的家人、亲人乃至子嗣,史书没有记载,但相信是有的。“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国破族亡之际,作为太子的他,岂能没有危机感,传宗接代、延续血脉必是本能的愿望和当务之急。
鄯月光的墓志铭上,写着鄯月光是已故车师前部国王长子之妻。车师前部地处准噶尔盆地东部天山南麓的谷口,是中原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与鄯善国地望相邻,互为婚姻,是很正常的事。专家研究称,这件志文中“虽不显前部王子的名字与事迹,但其妻既葬于洛阳,则王子亦必寄居于洛无疑”。鄯月光夫妇或以质子,或以就学的身份流寓洛阳,死后也葬在了洛阳。
三位鄯氏先祖墓志铭的发现,对于我们寻根姓氏源流有着无可估量的史学价值。特别是目前看到的鄯乾墓铭,全文418字,不仅概述了他一生的曲折经历,还写到了他的父亲、祖父两代鄯善国王的基本情况,让我们鄯姓的后人既觉得格外亲切,又生出莫可名状的愁思和怅惘。无疑,鄯乾这个事件无论对于古代的鄯善国还是对于后代的鄯氏族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意义。于鄯善国而言,鄯乾由王孙沦为人质,表明鄯善国已到末世,纵未亡国也不久矣;于鄯氏族人而言,这是长期地处西域的鄯氏一族流寓并定居中原的起点,也是王族国姓走向民间的肇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任谁衮衮王公,终难耐滚滚红尘。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在摧毁中获得重生。
溯至北魏(公元五世纪),我们已经回望了1500年。至此,皇后村鄯氏的历史脉络,虽未能说严丝合缝,历历可辨,却也算是草蛇灰线,有迹可循。
(转自《新盂县》 )